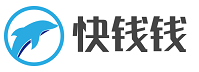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英美等国城市建设风潮影响下,中国城市改变传统封建城市旧貌,开始向现代都市转变,市政进步、人口增加,城市繁华日显。然而,伴随城市发展的同时,由于水利建设滞后,城市内涝灾害频发,成为遏制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瓶颈。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欲将“首都”打造成世界知名的国际都市,遂开始进行以完善基础设施为主的市政建设,城市水利设施被列为基础工作。为消除城市内涝灾害,该市政府改建市内下水道,修复排水设施,制定防水措施,凡此种种,无疑均是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城市建设研究,多从城市史或历史地理的角度切入,对其洪涝防治工程关注不多。有鉴于此,文章拟从环境史的角度对南京城水灾原因进行分析,对国民政府时期城市排水工程与防水措施作一些实证性的研究,总结民国南京城市水利建设的成败得失。作为前车之鉴,这一时期城市水灾的应对与治理对我们当今市政建设仍有重要的启示。
一、南京城洪涝灾害及其成因
南京城位于长江之畔,享有江河运输之利,但每年汛期长江水位高涨,城内积水受江潮顶托无法排泄,诱发水灾。南京地区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过境飓风影响,会出现强降雨天气。时间短,雨量大,城内积水排泄受阻即演变为城市内涝,往往“一日之内,可以观潮汐之涨退。”姚莹的《江宁府城水灾记》描述过南京城水患时的情形:“五月复大水,阛阓深六、七尺,城内自山阜外,鲜不乘船者,官署民胥在水中,舟行刺篙于屋脊。”魏源目睹灾情,作《江南吟》哀叹城内灾民的凄惨遭遇:“江潮挟淮城倒灌,一闸难加万马奔。城南移定走城北,月华照城如泽国。船撑桥顶鸡栖树,父老百年来传说。一岁潦尚可,岁岁淹杀我。南北六朝都江左,几见金陵之城水中坐?”
民国前期,南京城水患日趋频繁,频率高、损失大,每逢大雨,南京城“尽成泽国”,“积水成渠,数日始能宣泄。”1915年6月下旬,降雨量达406毫米,多处街道被淹。次年6月中旬,连续两日阴雨,“城内低凹之处几成泽国,房屋电杆被风吹倒甚多,三牌楼至丁家桥一带铁道淹没,交通停滞......东水关城墙崩倒。”1918年夏,大雨过后,秦淮河水溢出河道,泛滥横流,地势低洼处受灾。1921年8月16日夜,阵雨过后“城内低凹处全被淹没,电杆房屋民船损坏无算”,“学校公所以及居室之内,可以观潮汐之涨退。”1922年9月29日,暴雨过后江水高涨,城内河道因江水顶托,积水无法排泄,内涝严重。1923年5月,大雨导致秦淮河泛滥,花舫生意被迫中断;7月上旬,“霪雨三昼夜,行人裹足,秦淮河一带水已上岸,一般苦力及小本营生者均苦之。”13日晚大雨,城内河道水位猛涨,溢出河床,顺势乱流。1925年7月2日至3日,降雨141毫米,城内积水如河。1931年大水,南京城珍珠河两岸低洼地带、通济门至西水关一带、夫子庙、成贤街、铁路两旁民房均被水淹,“地势稍高者,亦水深没胫,低者竟没膝矣,市府亦水深没胫。”水灾给南京市带来巨大损失,“街道浸没,房屋坍塌,村落如海岛屿,灾民则与虫鸟竟争同栖树头。”据统计,南京持续降雨23天,降雨618毫米,全市受灾户总计为2871户,难民11838人,损坏房屋4171间,倒塌墙壁约793处。1933年7月9日,雷雨过后,“城内洼处马路,积水甚深,低地居民有浸水者”,27日晨,大雨过后,南京城区“较低洼之街道一度泛滥。”水灾带来严重损失,“商店停市,交通不便,米粮来源几于绝迹,学堂亦因水隔断不能上课。”
气象等自然因素如降雨量、季风气候以及高山低地镶嵌其中的地理形势都可能影响水灾的发生。但是,人为治理因素亦不可忽视。正如南京市政府参事张剑鸣所言,“由于未及预防,以致水势骤发,遂难遏制”。由此可知,城市防水建设的缺失是南京城区内涝频发的主要原因。笔者以为,这一时期导致南京城内涝频发的人为因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南京城被明城墙环绕,城内积水主要依靠秦淮河排泄:雨水、废水流入秦淮河,通过城墙底部设置的水关、涵闸排入长江。清末至民国,城内水利荒废,水文环境恶劣,两岸百姓“弃灰土瓦砾者率于河,是以日淤垫几成平陆”,西水关附近河道“河底较东水关外约高二公尺有余”,秦淮河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河。1927年8月25日的《申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寄新都友人的信》的文章,道出了一位外地游客游览秦淮河后的感受:“一朝亲临不免令人失望,污秽臭腥的沟水,简陋狭隘的房屋,一到了这地方就使你伤心失意,只觉得软绵绵地如坐在一个污秽的烂絮筐里......”狭窄淤塞的秦淮河成为臭塘死水,失去防洪功效,九华山及城内高地雨水汇入河道后无法排泄,以致“山水暴涨,稍一不慎繁区立成泽国。”
此外,城内其他河道,如青溪、玉带河、九华山沟、珍珠河、香林寺沟等作为秦淮河分支深入城区各处,犹如城市的排水管道,收集雨水、污水后汇入秦淮河。民国前期这些支河径流大多淤塞浅狭,无法排泄雨水。九华山沟、玉带河两处河道淤浅,九华山来水下泄后无处排泄,山水四散乱流,“成贤街、中央大学积水数尺”即因此而起。白鹭洲地势低洼,河堤处原设有水闸防水,民初闸废,该地水患皆因“金陵闸废弃而河水尽入”所致。黄埔路原有前湖入城水道,此河道也是香林寺支流必经之地,该河道阻塞后,雨水无处容纳,遂泛滥成灾。
南京市原本河塘众多,这些河塘可以蓄水防洪,在防治内涝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城市移民的迁入,生齿日繁,房屋建筑不断增加,为适应发展需要,许多沟渠塘河被人为填塞掩埋。剩余池塘皆为死水,塘水不流通,废物充斥其中。当时城市垃圾还没有较好的处理方式,市政府决定“利用垃圾将市内各废弃池塘一律填平”,想在处理城市垃圾的同时一并解决死水臭塘问题。水塘被填埋,潴水防洪作用消失,而相应的排水设施未能同时跟进,雨后市区积水无处瀦蓄,引发城市内涝。工务局指出:“房屋增加,原有水塘渐次填塞,污水无处宣泄,秽臭湫湿。”市政府对水灾调查后认为,“新街口及破布营一带水灾,因水塘填塞致局部积水无法宣泄所致。”
秦淮河与长江水位涨落关系密切,长江水位低于西水关时,城内河水可由秦淮河排入长江;当长江水位高于内河水位时,需关闭东、西水关水闸以防江水倒灌。东、西水关水闸正是关系南京城安全的重要水利枢纽,但民国前期原有闸门“已失效用,即以不能关闭,致江水向城内灌入,泛滥市内。”江水倒灌加重南京城区内涝灾害的危害程度。
玄武湖湖水下泄是引发南京城水患的因素之一。明城墙外,湖西北处原有河道与长江相接,至清末,河道已废。湖水出路仅有台城水闸一处,通过明城墙底部河道泄入秦淮河。玄武湖与城内地势落差较大,湖面高出秦淮河一尺有余,每年雨季,为防止湖水大量下泄需关闭台城水闸,但是,湖水仍从城墙底部及地下孔道渗漏流入城内,涌向成贤街一带,加重灾情。
南京城早在六朝时就设有排水暗沟、明渠,收集地面雨水、污水进入排洪河道。1987年,南京考古队挖掘出位于草场门一条明代砖砌下水道,该下水道由主排水道和分排水道组成,从城墙底部穿过,将水排入秦淮河。下水道遗址的发掘说明,明朝时下水道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市政设施。迨至民初,水利废驰,沟政不修,百姓“将废物倾入,宽度深度历年减少”,原有下水道设施湮废破败,“平时臭气四溢,大雨则温溢街巷。”
以上史实表明,南京城原有水利设施存在严重隐患,河道淤塞、河塘填埋、水闸废弃、城墙渗水,水利设施破败及水文系统紊乱致使城市水患发生机率增大;河道失修、未能防患于未然等人为治理的缺失加重了城市内涝的灾害程度。
二、市政府防治内涝措施
近代南京城防水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灾后治理到灾前预防且逐渐完备的建设过程。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作为国家重建与民族复兴的重要象征,国民党对首都南京的城市建设颇为重视,聘请技术专员拟定城市发展规划。在国民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南京城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快速展开,然而无论是何民魂时期的《首都大计划》还是刘纪文负责起草的《首都计划》,都对城市排水建设缺乏足够重视,直至1932年后,在城市灾害频发的发展因境下,市政当局才将市政建设重心转移到防水建设中来。
1927年市长何民魂推出了第一部南京城规划方案——《首都大计划》,提出首都建设实现“科学化、艺术化、农村化”的发展构想,其内容涉及交通与分区建设两方面,却未见对城市水利建设的具体规划。后因何民魂的桂系背景及蒋桂政争中桂系的失败,被迫辞去市长一职,取而代之的是亲蒋人物刘纪文。刘氏就职后,立即推翻前任市长的规划草案,成立以已为首的市行政委员会,设立工务、公安、教育、卫生、公用五局。1929年在他的主持下《首都计划》出台,其内容包括道路管理、住宅、卫生、学校、工业、人口等诸多方面,并涉及城市河道整理、铺设下水管道等城市水利建设等内容。刘纪文深受西方近代市政思想熏陶,在他主持下,南京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尤其在道路建设、城市供水、公园绿化、照明及通迅等方面成效明显,进步显著。但令人遗憾的是,《首都计划》对于城市排洪规划粗糙简略,首都建设初期,城市防水建设未受到足够重视,城市灾害频发成为制约都市发展的瓶颈。
美国飞行员林白拍摄的南京郊区鸟瞰图
内涝频发使城市发展受挫,尤其是1931年大水灾后,当局者最终认识到排水设施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都市结构,譬如人身,华冠盛服,而肺腑之宣泄不灵,则疾病生之矣,故下水道者,都市之肺腑也。”至此,城市排水建设被摆在突出位置。在国民政府主导下南京市工务局开展了以修复城市水利设施、建设和完善城市排水系统为核心的城市水利工程建设,制定防水计划、实施下水道工程、确立防洪预警机制、在预防水患、防止城市内涝方面稍显成效。
1932年南京市工务局召集水利专员,勘察南京市水利环境并拟定《南京市防水计划报告》,以应对每年汛期可能出现的城市内涝。报告指出,加强城市水利建设,应疏浚城内河道,铺设下水管道,修复城市水利设施,“使城外之水不能浸入,而城内之雨水又可以排出,以避免城市内涝的出现。”在这项提议下,以疏浚河道、修建排水管道为主的城市水利建设渐次铺开。
(一)修复南京城排水设施
秦淮河横贯南京城,是城内重要的泄洪河道,对城市生活用水、消防、防洪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防水计划报告》对秦淮河排水功能给予充分肯定,“该河一方可藉雨水之宣泄,亦可减少渠道建筑之费用,乃将城内秦淮河及城外护城河一概保留而改良之。”这一决策为秦淮河及城内其他河道的疏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1932年市工务局水利专员对秦淮河水利环境实地勘查后指出,“河水污浊,河身淤塞以致水无所泄,泛滥成灾。”同年3月,内政部第一次民政会议作出“秦淮河上下游同时挑浚,以利宣泄”的决定,指定由南京市政府与江苏省政府共同办理。6月,“疏浚秦淮河设计委员会”成立,“委员会”隶属于南京市政府,由水利专家及市政府参事组成,有议事之责但无行事之权。“委员会”制定秦淮河治理的具体方案,再由市工务局负责实施,其委员包括国民政府顾问德国舒巴氏、市参议员陈公哲、工务局长张剑鸣等人。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秦淮河关系南京城的水利安全,秦淮河淤塞是诱发城内水患的因素之一,“疏浚整理,刻不容缓”,建议市工务局立即对东水关、水西门等处河道疏通开浚,并修缮东、西水关闸等水利设施。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于1932年编制的《扬子江淮河流域水灾地图》
市政建设涉及道路交通、住宅、通讯等诸多方面,而南京市财政捉襟见肘,治理经费未能落实,疏浚工程一再延迟,秦淮河淤塞的水利局面迟迟不能改善,旱涝灾害交替发生。1933年夏,雨后南京城“积水甚深,低地居民有浸水者”,“较低洼之街道一度泛滥。”1934年大旱,秦淮河断流,部分河段成为臭塘。“江宁、句容、溧水一带,因赤山湖之淤垫及秦淮河之淤塞,历年被灾甚深。”秦淮河失浚引发的环境问题也超出了南京城的地域范围,并造成该流域内的农业生产危机。为缓解旱情,同年9月,省建设厅拟定《旱灾工赈施工计划》,“指拨水利公债四百万元,疏浚江南各县河道”,并将秦淮河疏浚列入施工计划之内。至此,秦淮河等城内河道疏浚工作终于进入实质阶段。1935年6月,省建设厅采用以工代赈方式,招募民工3万余人,完成秦淮河疏浚工程,秦淮河的水文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城内秦淮河与长江相通,连接长江与秦淮河的东、西水关,犹如“水管子”的“阀门”,如不将其锁住,秦淮河畅通后更易使江水倒灌,江水顺河道涌入城内引发内涝。为此,在这次水利建设中,“委员会”特别强调要修缮城内重要水利枢纽。在此提议基础上,水闸建设工程快速展开,同年秋,水闸建成,采用钢筋混凝土构造,下设混凝土闸基,新建水闸有效阻止了江水倒灌,城内水患风险降低。
(二)制定下水道排洪方案
下水道建设是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城市排水体系建设中的重点工程,这对于改造城市污水四溢,雨水泛滥的水利环境具有重要意义。1929年《首都计划》第一次将排水系统列入城市整体规划之内,计划称“渠道为宣泄雨水及污水必需之具,......故近代都市,莫不注意于渠道之规划。”但该计划仅是简单的规划大纲,对排水管道的标准、防洪方案并未详细设计。市政建设之初,有限的经费被投入到公路、住宅、电力等设施的建设,财力拮据致使“南京城下水道工程久久未能上马建设”,内涝灾害一时难以根治。南京既为国民政府首都又是国民党的权力中枢,城市内涝频发不仅使国民党打造南京城国际都市计划受挫,更被批评执政能力不足。社会舆论及城市灾害频发的双重压迫促使南京市政府加快下水管道的建设步伐。1931年作为首都建设最高主管机关的“首都建设委员会”在给国民政府的电文中称,将在委员会下设立“下水道筹备处”,专事负责下水道建设事宜,但是这一提案随着人事组织的更迭而不了了之。1933年国民政府将荷兰庚款退款的65%用于南京市排水工程,作为铺设下水道与城内河道疏浚费用,在充足财政的强力支持下,“首都排水工程”终于全面展开。随即,南京市政府成立下水道工程处,组织人员勘查地势,设计方案。南京市地理格局呈现北高南低的走势,以鼓楼高岗为界,划分为城南城北二区。城南区地势低洼,人口密集,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城北区地高人稀,雨后雨水顺势流向东南一带,城南区常泛滥成灾。下水道工程处在综合考查人居密度、地理形势等因素后,决定先从城南区建造下水道。经过为期2年的筹划,1935年《南京市城南区下水道工程计划》出台,这是南京市制定的第一部较完善的现代化下水道排水规划。该规划对影响下水管道排洪的相关因素如降雨量、积水量、积水流速进行测算;对水管横断面、管内流速、小阴井、阴井距离、水管质量、管材、抽水机等出严格规定,整个工程预计所需经费500余万元,限期3年完成。为防止短时间内出现大量降雨导致城内积水,在设计之初工务局对下水管道型号作出要求。以二十分钟可能达到的最大降雨量为标准设计排水管内径,“使某一区域流水通过水管之时间,等于该区域内最大雨量之集中时间”,这一设计即是针对可能出现的暂时性城市内涝制定的。
城市排水主要针对雨水和污水,工务局因此制定了“分流制”与“合流制”两套方案。分流制是将城内雨后积水经管道排入秦淮河后泄入长江,生活污水则经专门污水管道排入城外污水处,作统一处理;合流制即将污水和雨水泄入同一管道进行排放。分流与合流两种方式,如何选择?分流制存在两个弊端,首先,分流制需铺设两条下水管道,经费开销大;另外,雨水较大时,仍会有污物混入清水管道,“虽名为分而实不能尽分”。合流制可节省经费,只需铺设一条管道即可同时完成污水和雨水的排放。降雨时,将城内雨水与污水排入同一管道,生活污水经雨水冲刷稀释后排入秦淮河;无雨时,将秦淮河处的排泄口封闭,污水进入截水管流入水西门,经抽水机排入长江,“虽名为合,而实则清浊判然。”时任工务局局长的宋希尚认为,“何者宜用,选择标准,不外二种,一则根于经济,一则计其功效。”可见,经费的制约与排水功效是作出抉择的重要标准,很显然,分流制并不符合“节俭与实效”的建设原则,工务局遂采用合流制方案铺设下水管道。
1935年6月,城南下水道工程正式动工,经过为期两年的努力,至1937年南京市共埋设下水管道26722公尺。但部分管道铺设后还未来得及使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工程被迫中断,城北区的下水道工程也就无暇顾及了。
(三)确立防洪预警机制
民国前期,南京城内涝频发且造成严重损失,而下水道工程迟至1935年才正式施工,在这期间,如何应对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的城市内涝,成为市政府首要解决的城市危机。自1931年大水后,长江流域防洪工作受到重视。1932年,“扬子江整理水道委员会”对长江下游各险要堤段进行实地勘查,组织人员修补江堤缺口。与此同时,“为防患未然,免除水患”,行政院通令沿江各省作好防洪工作,严令禁止挖堤取土等有害大堤安全的破坏行为。同年,南京市政府颁布《南京市防水计划草案》,要求工务局对秦淮河、进香河等城内河道疏通开浚,维修武庙及东、西水关防水闸门,修复明沟暗渠等旧有排水设施,保证行水通畅。这次治理对市内河、湖、渠、塘进行了统一疏浚。汛期在江堤码头、东西水关“备办大批沙袋洋松,以备堵塞之用”,应对可能出现的洪水灾害,南京城市的防水能力明显提高。
1935年6月,“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议定,当长江水位涨至5.5公尺时,各市进入防洪阶段,由地方政府主持防洪工作;水位涨到7.2公尺时,为危险时期,届时中央政府会派水利专员协助地方政府进行防洪工作。同年7月,长江水位猛涨,洪水来袭,形势严竣。南京市成立专门负责城市防水事务的“防水工程委员会”,“全体委员分为两班,日夜轮流值班,观测水势变化。”在水利枢纽如东水关、下关码头等地配备充足的抢险材料,如“运输汽车、抽水机、防水沙袋”等以便随时调遣。另外,由“宪兵司令部、教导总队、警察厅、市党部及市商会”共同组织成立“首都各界防水委员会”,协助工务局监督水势涨落,配合防洪抢险工作。在“首都各界防水委员会”协调动员下,“警察厅、教导总队”等机关调派千余人,分别驻守在新河口、北河口、东水关等处;在燕子矶区、上新河区、大小黄洲等地指派技术人员分段负责,现场指挥。各区公所将水位记录随时上报给“防水委员会”,由“委员会”进行统一调度。7月8日,长江水位达到6.9公尺,距规定危险阶段仅差0.3公尺,“为防患未然,免蹈二十年(1931)覆辄起见”,“防水工程委员会”立即开展防洪事务。为防止江水倒灌,工务局关闭东、西水关闸门,将铁窗棂、铜心管、半山寺、台城闸门及凡城区与江水相通各沟洞全部堵塞;在东、西水关、武定门安置多台抽水机,将秦淮河水抽入长江,如此,既阻止江水入侵又将城内积水排出。对于这次预防,市工务局认为,“即使续降大雨,亦可随时排泄入江,当不致有泛滥之虞。”防洪预警机制的确立和洪水监测系统的完善,使散布在各处的防灾人员能够及时掌握水文变化,作到灾前预防、灾中跟踪,城市内涝的应对能力大大加强。
三、民国南京城市内涝防治成效
独特的自然环境加之人为治理的缺失是民国初期南京城内涝灾害多发的两大诱因,而水利治理上的不作为才是城市水患发生的根本原因。城市排水系统的完善和积极的灾前预防可以有效阻止城市内涝的发生,1935年城市内涝的消除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1931年水灾,南京段长江水位高达7.6公尺,受江水顶托影响城内积水无法排泄,城区东南部、成贤街、夫子庙、励志社、武定门、秦淮河两岸、下关热河路兴中门至车站一带,全被水淹。1935年江水倒灌入城的危险程度并不逊于1931年洪水,长江水位涨至7.2公尺,“较二十年最高水位7.6公尺,相差甚微”,“经筹划防堵抢救,幸得转危为安”。由于防洪机构的积极应对,水灾化险为夷。在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参与治理的综合作用下,抗战前南京市政府在防治内涝过程中初步建立起“防洪预警机制”,并成功遏制了城市水患的发生。同时,这也表明,南京城内涝灾害尽管因天气变化所致,但是,人为正确治理对水灾危害具有决定性作用,防患于未然与临灾时的科学应对必然能够极大地减轻灾害程度。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首都”建设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其发展之路转入了以“建成模范城市和国际都市”为取向的新轨道,与之相匹配的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之一的城市水利建设成为市政建设的核心内容。这既符合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也满足了南京市民改善城市面貌的要求。在东水关建闸、铺设下水管道、完善城市排水体系等多项水利工程逐步实施的基础上,水利设施的防水功能逐渐恢复,内涝灾害风险降低。1934年南京市政府启动“首都防水规划”,南京城排洪能力增加。尽管1935年、1936年春夏之交南京地区最大降雨量仍未低于200毫米,但却没有形成严重内涝,这与国民政府加强城市水利建设力度密切相关。抗战爆发后,已经修复的排水系统遭到破坏,城内积水难泄,城区水灾再度频繁上演。
这一时期南京市的水利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城市水利环境仍不乐观。市政府虽然制定了科学的排洪方案,但因经费制约,下水道工程被长期搁置,至1936年仅完成城南区的管道铺设,“虽臭气已较过去减少,但仍未达到根本清除的目的”,后因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城北区的下水道规划未能付诸实施。南京市政建设虽“无日不在进步之中,但这种进步都是迂缓而不迅速。”1936年一篇题为《朱梅》的文章中写到:“和南京离开已经快五年了,五年来的南京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马路已比从前加多,街道也比从前整齐,只是秦淮河还是臭水一沟......”对此,市长马超俊坦言,市政建设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大多数居民生活仍处于简陋困苦之中,南京城建设已经不是地区性的或逐渐改善的问题,而是必须经过全部检讨,加以彻底调整改善。”南京城市水利建设的实际效果与最初设想仍存有差距。
财政支绌和组织机构的频繁变更制约了水利建设的有序开展。因税收分配制度限制,南京市政府财力孱弱,国民政府的财政补助成为维系市政建设的主要经费来源。受30年代初经济危机影响,以及国民政府为剿共投入大量军费开支,遂使中央政府对“首都”建设的财政补助越来越少。城市建设千头万绪,市财政入不敷出,城北下水道工程被长期搁置,秦淮河疏浚也一再拖延。另外,南京即为国民政府首都,行政系统庞杂,市政机关备受掣肘,既定规划难以按部就班的开展。马超俊感叹道:“市府一切设施常为少数人所轻视,以为地方机关之政令可不必受其限制......本市处于首都最小机关之地位,一切庶政,推行不易。”城市建设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朝令夕改及重叠臃肿的行政系统不利于市政建设的快速发展,南京市早期现代化建设可谓任重道远。
在南京城早期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政建设被认为是影响国家形象与政党执政能力的政治工程,国民党也将首都建设视为民族复兴的重要象征,因此,公园、林荫大道、城市广场等显而易见的形象工程发展快速,相比之下,被视为城市发展生命线的防水设施则进展迟滞。考察民初南京城内涝灾害成因可知,水患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失于防范才是诱发城市灾害的主因。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初期,城市建设虽取得一定成效,但防水建设的缺失决定了城市发展的内在限度,也制约着国民党打造南京国际都市的美好意愿。与此同时,执政当局在防治城市水患的过程中,对城市排水建设重要性认知逐渐取得共识,排水设施既是市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城市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其质量优劣也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高度的重要标准。至此,南京市政府开始调整规划方案,将市政建设的重心转移到水利建设中来。不过,对于南京这类依靠国家权力推动转型的城市而言,因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城市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故受政治波动影响明显。政府的控制与监管固然对南京城市现代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抑制因素,南京作为国民党的权力中枢,国家组织、官僚、军队汇聚于此,机关林立、派系倾轧,市政府权力备受掣肘,财政捉襟见肘,水利建设几经挫折,虽有成效却远未达到设计之初的既定愿望。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城市建设被迫中断,城北区的下水道规划未能付诸实施,但是作为当时城市建设事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仍反映出当时城市规划者、建设者打造国际都市的远大目标。
来源:本文选编自胡吉伟《抗战前南京城市内涝成因及其防治》
原载《兰州学刊》2014年第10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